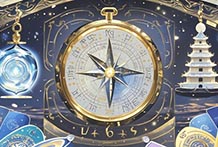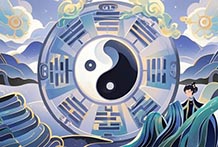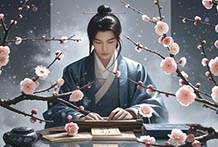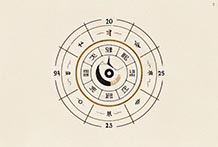圣人之心实与天地同妙,应该从天道自然无为的角度来领会圣人之心
在邵雍看来、心有三种,一为天地之心,二为人类之心,三为圣人之心。天地之心即太极一元之道,是一种尚末被人们所认识的客观自在之理,为天运之本然,阴阳之消息,属于所知的范畴。人类之心则属于能知的范時,具有主观能动的灵性,能够认识天地之心,把自在转化为自为。《观物内篇》说:“大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与!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与!”这是认为,天地之心的特点在于〝一动一静〝,人类之心的特点则在于〝一动一静之间”,加上了主体性的因素。天生于动,地生于静,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万物由此而生,大化由此而出,自然而然,无思无为,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就是天地之心的本质。

人类之心则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动中含静,静中含动,处乎一动一静之间。《庄子 •在宥》曾说:“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市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这种主体的能动性就是人类之心的本质,其所以称之为“至妙至妙“,是因为只有凭借着这种主体的能动性,才能发挥人事之用去感应和认识自然而然的天地之心,把人类从物类中分化出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
但是,人类之心也包含了很多的杂质,有情有欲,有情则蔽,蔽则昏,有欲则私,私则“屈天地而徇人欲”,因而免不了常犯错误,产生”心过”。邵雍满怀感慨地指出:“无口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学?吁!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语心哉!是知圣人所以能立于无过之地者,谓其善事于心者也。”(《观物内篇》)圣人是人类中的出类拔萃者,圣人之心集中体现了人类之心的精华而无任何的杂质,至诚湛明,精义人神,能知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贵之,因此,只有圣人之心才能全面地认识天地之心,人与宇宙自然的沟通是以圣人之心为中介而后实现的。关于圣人之心的本质,邵雍指出:“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观物外篇》)
所谓无思无为,即先天之体,也就是一动一静的“天地之至妙〝,圣人心无一思之起,亦无一为之感,一而不分,退藏于密,则与先天之休合而为一,由此发而为后天之用,随乎天地,因时之否泰而进行人为的因革损益,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这就是处乎一动一静之间的“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了。《观物内篇》说:“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 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这就是认为,圣人之心实与天地同妙,应该从天道自然无为的角度来领会圣人之心。但是,圣人之心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因素,以后天之用为主,能开不世之事业于无分,所以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价值理想的完美的统一,是人性的最高的典范。
在《伊川击壤集序》中,邵雍对自己 的性命之学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表述。他说: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关。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

朱意对这几个命题颇为赞赏,认为“此语虽说得相,毕竟大概好”,曾与他的学生反复讨论。(见《朱子语类》卷一百)道即天地万物自然之道,无所不在,在物谓之理,具于人谓之性,就外延而言,道大而性小,性从属于道,就内酒而言,则道小而性大,因为人之性除了同于自然的物之理以外,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的规定。
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说,欲知此道之实有者,当求之吾性分之内,故称性为道之形体。性之本质为善,具于心中,心为性之郛郭,心大而性小,心包括性,性不能该尽此心,因为心统性情,有正有邪,善恶相混,故心伤则性亦从之。身者心之区宇,心是身的主宰,身是心的寓所,此二者相互依存,不可脱离,如果身体受到伤害,也势必要伤害心灵。身体的生存必须仰赖外物的资养,故物为身之舟车,如果缺三外物的资养,身体的生存也就失去了保障。
这几个命题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把性命之学放置在整个宇宙的大系统中进行宏观的考察,既突出了人性高于物性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同时又强调这种人文价值的本源在于自然之道,人性的完美的实现必领与作为物质范時的身体、外物结成和谐的统一。
根据这种表述,邵维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说:
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末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矣。(《伊川击壤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