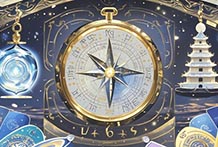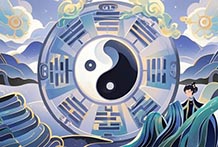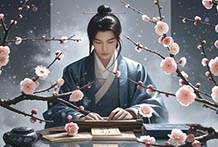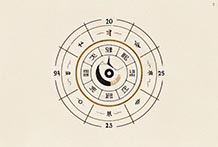唯有圣人之观物,才能表里洞照,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
就邵雍的哲学而论,他并没有否定名教之乐,只是把名教之乐置于第二位、使之从属于观物之乐。照邵雍看来,名教之乐着眼于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文的价值,“治则治矣,然犹末离乎害者也”,可以管束人的身心,做一个道德人,但不能使人免除情累之害,做一个宇宙人。观物之乐则是把人提开到宇宙意识的高度,可以做到“两不相份”,“情累都忘”,既不损告对事物的客观的理解,也能完整地维护人所应有的名教之乐。这是因为,以物观物的本质在于以物喜物,以物悲物、人之悲喜发而中节,合乎物理,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感应,而无丝毫的情累之私。因此,为了维护名教之乐,使之能够更好地安身立命,不可目光短浅、局限在名教的本身上做文章,而必须从事高层次的哲学研究,以物观物,对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去追求观物之乐。邵雍写了一系列以《观物吟》命名的诗篇,略举数例,以宛见他所谓的观物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他说: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皇王市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飞走草木类既別,士农工商品自成。安得岁半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伊川击壤集》卷十)
时有代谢,物有枯荣,人有衰盛,事有废兴。(卷十四)
地以静而方,天以动而圆。既正方圆体,还明聊静权。静久必成洞,动极遂成然。润则水体具,然则火用全。水体以器受,火用以薪传。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卷十四)
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卷十六)
一气才分,两仪已备。國者为天,方者为地。变化生成,动植类起。人在其间,最灵最贵。(卷十七)
画工状物,经月经年。轩鉴照物,立写于前。鉴之为明,犹或未精。工出人手,平与不平。天下之平,英若于水,止能照表,不能照里。表里洞照,其唯圣人。

察言观行,周或不真。尽物之性,去己之情。(卷十七)
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能将一个字,善解百年述。
物理统开后,人情照破时,情中明事体,理外见天机。
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难。(卷十九)
由此可以看出,邵雍所观之物,包括天时地理人事诸多方面,也就是由天地人所构成的整个的世界。观是一种客观的理性认识活动,不是指人的道德修养。观这个概念本于《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武。”《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群下》:“古者包酒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 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邵雍据此而提出了观物的思想,以观物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他把观物比喻为以鉴照物,能知之监与所知之物是一和反吹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是,监之工制,精粗不一,有平与不平,常侦所照之物的真相受到歪曲。天下之平,莫若于水,清明止静,肖物唯一,但是,水仅能照
表而不能照里,只反映了物之表象而未深人其本质,唯有圣人之观物,才能表里洞照,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以物观物,尽物之性,去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