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学与《周易》:医家在战乱年代与疾病斗争中获取的治疗经验
约在公元 1115 年,女真族占领北中国,建立了金帝国,同时,宋王朝被迫南迁,于1127
年建立南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随后,又由于北方蒙古族兴起,先后灭金、灭南宋,于1279年建立了统一的元帝国,前后约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元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饥饱失时,加之劳役过重,因而普遍体质虚弱,抗病能力极度低下,导致疾病流行。当时的医家在与疾病做斗争中,大大丰富了治疗经验,从而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医学理论。特别是在当时社会上唯物主义思想和改革风气的影响下,认为〝古方今病不相能”,主张根据实际创立新方。号称“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各自根据医疗实践,创立了各自的学派,形成了空前的学术争鸣,从此医学理论为之一新,医道为之一振,并给后来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张、李、朱四大学派的产生,是与当时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但有的人却忽视了这一客观实际,认为四大学派的产生与“五运六气”的周期性有关,即所谓“凡六十岁为一周”的“大司天”理论。如清末阽懋修说:“•…仲景之用青龙、白虎也,以其所值为风火也;守真(刘完素)辟朱肱用温之误,申明仲景用寒之为已效方三一承气也,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东垣(李泉)以脾胃立论,专事补脾者,以其所值为寒湿也。丹溪(朱震亨)以知柏治肾,专事补阳者,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世补斋医书》)这一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令以上诸家学说主张与“大司天"周期相一致,也只是偶合,并无必然性。况仲景既有用青龙、白虎的,也有用四逆、理中、真武的,按“大司天”说,岂不成了“风火”与“寒湿”同时当值了吗?不然,又将做何解释呢?

客观地分析,应该说,金元四大学派的产生,来自他们各自的医疗实践,而医疗实践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如刘、张、李三氏虽都处于北方,又都值战乱频仍之际,但具体情况却各不相同。刘、张二氏医疗活动的时间相差不远(刘公元 1120~1200年,张公元 1151~1234 年)都值烽烟四起,社会动乱,急性热病流行之际,故刘氏在其实践中认识到六气致病以火热居多,主张用寒凉药治疗,成为寒凉派的代表;张氏推崇刘氏学说,并根据自己在实践中以外感病居多的特点,临征治疗主张以攻邪为主,成为攻下派的代表;李氏则较晚出 (1180~1251年)手刘、张二氏,当时的实际是,人们在长期战乱中,饥饱无常,劳役过度,以内伤疾病居多。他曾在《内外份排惑》中与道:“大抵人在围城中,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月,胃气亏乏久矣。”这就是他以内伤疾病为主,专重脾胃的由来,因而成了补士派的代表;朱震亨(1281~1385 年)的医事活动在元代,时间最晚,且在南方(浙江义乌即金华),地方较富庶,又少战乱,人们生活较安定,但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而导致相火妄动,病阴虚者多,故主张治疗以滋阴为主,成为滋阴派的代表。于此可见,以上四大医家的不同学说,都是来源于他们各自的医疗实践,也就是说,他们的学说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直到现在,仍受到广大中医工作者的推崇。但是,他们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各从一个侧面去南述一个方面的理论。因此,对四大家的不同学说特点,必须容观地分析和理解,取各家学说之长,因人因病制宜地研究和运用,才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反之,如果从主观认识出发,或宗刘而非李,或扬张而抑朱,都是十分有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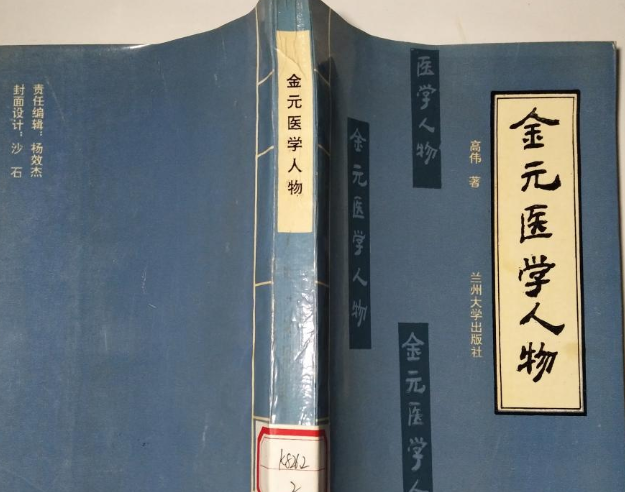
另外,以上四家,虽是在各自的医疗实践中创立了各自的学派,然其学术思想莫不洲源于《灵》《素》,取法于天地。如刘完素云:“夫医教者,源自伏義,流于神农,注于黄帝……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也就是“天人相应”的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是《易》与医共有的。“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本源则归于一致。张从正也每用《易》理解释医理,如论人身则分天、地、人三部,以符《易》之三才;论方则取《易》“方以类聚”之义,申言五方用药各殊;论三消则曰:“八卦之中,离能烜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论证“三消当从火断。”(《儒门事亲•三消当从火断》)李果则按《易》“仰观俯察”“取物比象”之法,提出“人形象天”的命题,认为“人摄生防病,必须效象天地,法则阴阳。”朱震亨则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又以“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格致余论•相火论》)之象和“吉凶悔吝生乎动’之《易》理,认为“人之疾病亦生乎动,动之极也病而死。”(《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于此可见,刘、张、李、朱四大学派的学说主张虽各有不同,而其思想渊源则又是基本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