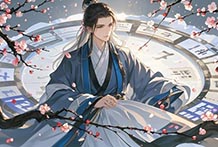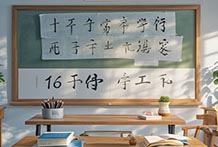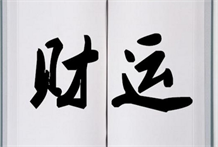岳总卿在《山斋愚见十书》(一卷)诸书曾论证《五行精纪》真伪考
文中提到的岳总卿,即为岳珂。据《宋史》卷四十一,宝庆3年(1227),“五月壬子,诏岳珂户部侍郎,依前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耐得翁系南宋后期的一个学者,撰有《都城纪胜》(一卷)、《山斋愚见十书》(一卷)诸书,此人原名及生平情况已不可详考,其中《都城纪胜》一书,序中所署时间为端平二年(1234年),与岳珂此序的时间(1228年)十分接近,可从一个侧面提供佐证,证明岳珂与《五行精纪》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耐得翁的这一记述我们还可以知道,《五行精纪》一书还是由岳珂予以刊行的,因此岳珂刊行《五行精纪》时给此书做序,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岳珂的这篇序文也是真实无误的。
《五行精纪》一书写成与刊刻后,对于它的著录一直是史不绝书。该书最早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阴阳家类"已有著录,称“《五行精纪》三十四卷”,陈氏在书目下还注明“清江乡贡进士廖中撰,周益公为之序。集诸家三命说”;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亦有著录,并征引了陈振孙的解题内容;到了明代,《文渊阁书目》卷十五中著录了本书;另外,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陈第的《世善堂书日》均著录本书为34卷,而叶盛的《菉竹堂书目》则著录为十册,董其昌《玄赏斋书目》虽有著录,但未说明卷册。从这些书目记载来看,该书在明代似乎还保存很完整,没有什么残缺。
到了清代,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代目录学家对本书的著录,都是一些抄本,而且卷数已有所缺失,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为32卷的抄本,一种为33卷的抄本。32卷的抄本,如钱曾的《述古堂书目》卷四著录本书为“廖中《五行精纪》三十二卷,五本抄",钱氏在《读书敏求记》中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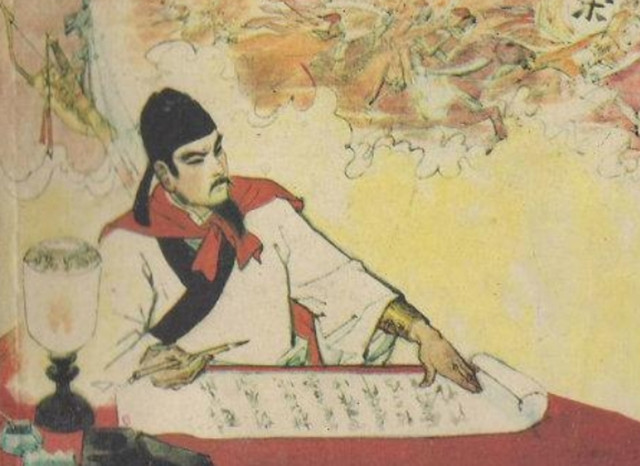
此书抄写精妙,又经旧人勘对过,洵为善本无疑。所引书五十一种,予所有者惟《珞琭子》,他则俱未之见。抚书自惭,何感与收藏家同埒乎。
另外一种《五行精纪》抄本则有33卷,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七著录有“《五行精纪》三十三卷精钞本”,并谓“《敏求记》所载只三十二卷,此较多一卷,所引星命家书五十一种,皆世不经见者”。另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著录的也是三十三卷本。”民国期间叶德辉曾在上海书肆上购得一个抄本,据叶氏自己云“卷与瞿目同”,也应该属于33卷的抄本系统。
根据以上史籍目录的著录以及藏书家的珍藏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五行精纪》一书从宋代就已开始著录,此后一直流传有绪,绝非后人伪作之书。虽然自清代以后,本书仅以抄本在国内流传,内容亦有所残缺,但该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目前在大陆所能见到的《五行精纪》旧有抄本,从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目录来看,似乎仅在国家图书馆还有收藏。国图的《五行精纪》抄本被分为善本与普通古籍两种,皆为33卷。经笔者对勘,它们都应是同一个来源,可能与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著录的抄本相关。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种抄本《五行精纪》从文物角度来说当然有很高的价值,是一个善本;但如果我们从其文献价值来看,这两种抄本由于并非全本,未免令人遗憾。而且,这两个抄本可能是由于抄手在抄写过程中恶意删减的原因,造成其现有的33卷中存在大量的脱漏和讹误现象,许多地方都令人不知所云,无法卒读。

从目前来看,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五行精纪》抄本因为内容上存在很多的问题,无法加以正确利用,®幸好该书在海外还有全本保存。2003-2004年,笔者在韩国延世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在韩国多家图书馆中读到了《五行精纪》一书。和国内情况不同,韩国保存下来的《五行精纪》全为古代的刻本而非抄本,在韩国多家公私图书馆,如韩国中央图书馆、国立汉城大学图书馆、延世大学图书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图书馆、全南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收藏《五行精纪》一书,只是其中有的图书馆所藏本书亦并非全本。
在这些收藏《五行精纪》一书的机构中,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有两种版本的《五行精纪》,一种共有5册34卷,该本每半页11行,每行20字,为一完整的刻本;还有一种则是每半页9行、每行17字,是该馆的贵重古籍,但只存一册,其内容是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本书是什么时候传入韩国,现在还不易确定;两种版本的刊刻时代亦未能确定,笔者初步判断该书是朝鲜李朝时期的翻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韩国著名文献学家李仁荣曾收藏有《五行精纪》一书的残本,他在所著《清芬室书目》卷六中著录有“五行精纪残本五卷 一册”,并说:
中宗、宣祖间木活宇印本,宋廖中编,存三十至四,四周单边,有界,每半叶十一行、二十字,匡郭长二一,八厘,广一五.五厘,黑口,册首有“月城李生"印记。此书活字与《俪语编类》小字略同。
根据李仁荣叙述的《五行精纪》残本的版式可知,他所收藏的这一残本与延世大学所藏的完整的34卷本《五行精纪》为同一个系统。李仁荣认为它是朝鲜时代中宗(1506-1544年在位)、宣祖(1567-1608年在位)年间的木活字印本,所论应该大体可信。这样看来,《五行精纪》很早就传到朝鲜半岛,并在当地被多次刊刻、传播和保存,这也可以说是中韩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