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数是纯数,它以奇偶结合卦象中的阴阳,具有象征性、多适性、不定性
易数是纯数,它以奇偶结合卦象中的阴阳,具有象征性、多适性、不定性。它不能用来精密计算,不可视为算术之数。但到了汉代刘歆的《三统历》,则把易数看作可计算之数,并应用于历法的历算之中,使易数在形式上成了制历的基本依据。按刘歆的说法,《三统历》的许多基本数据都是从易数中推出来的。
如:十九年七国,为什么呢?《汉书•律历志》说:“合天地终数,得闻法。”天数为1、3、5.7、9,终数为9,地数终数为 10,9+10=19,这样就确定了十九年该有七个国月。其实十九年七用是春秋以来“四分历”的成法,与易数毫不相干,此处明显是刘歆用易数附会,以神其历。
又如,《三统历》每月是 29天,即分每天为81分,所以 81 叫“日法”。刘歆以为81源于黄钟律管长(长9寸)自乘(即9×9=81),而黄钟律管的 9寸又源于“乾之初九”。所以归根到底,这81的“日法”是源于易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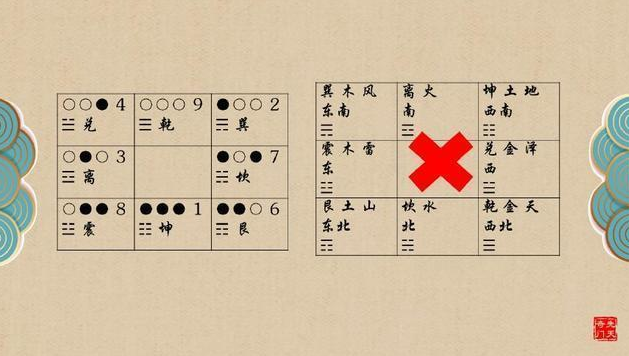
每天既分为 81 分,每月共有29x81+43=2392 等分,这个 2392 称为“月法”。
它是如何得来的呢?《汉书•律历志》说:“推大衍象,得月法。”具体推算是:
“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
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著之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国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而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列作算式即:1+2+3+4=10
10x5=50因“道据其一”,所以:50-1=49
以象两两之:49×2=98
以象三三之:98×3=294
以象四四之:294×4=1176
归奇象国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即加上 19 和1:1176+19+1=1196
再扐两之:119×2=238
这里每一个步骤紧扣大衍之数,乍一看是据其而来,但究竟有何道理,只有天晓得!如果用这样随意凑对的方法,任何一个整数都可以从易数中推导出来。换句话说,所有已知的整数历法数据,都可以用易数来加以证明,然后向世人宣布该历法的神圣与符合天意。很明显,刘歆是在搞数字游戏,不是由易数导出了历法数据,而是用易数去附会已知的历法数据。易数与实测的历法数据是格格不人的,将之强行地附会于科学历法是亳无神益的,只能带来徒劳无功的后果。

除刘歆外,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也受了易数相当大的影响。《系辞》中曾记载了“万物之数”,认为:“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是《周易》上下两箱64 卦334 爻的共有之策数(阳爻 36第,湖爻24第), 即38+2 ×(36+24)=11520 策。古人以为,万物之数,于此尽矣。而张衡写《灵先》,将天空中恒星的总数也归于此易数:“中外之官(指有名之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之数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
张衡创候风地动仪和浑仪,建立“浑天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天文科学家。他在易学方面造诣也很深,《灵先》之作就本之于《周易》之象,“浑天”之论,也汲取了《周易》的不少哲学思想。此处当他对似隐似显的众多微小星星数目进行推测的时候,又利用《周易》的“万物之数”进行概括,可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宇宙恒星要此易的“万物之数”多得多。易的“万物之数”如具指 384爻策数则是可计算之数,如真指万物之数则是不可计算之数。拿它来比附天上恒星之数,显然是错误的。但《周易》对于这位伟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唐代,一行也用历法去附会《周易》易数。他把自己有着许多创新之处的历法名为《大行历》,就是要向人们说明他的数据是从“大衍之数”中推出;来的。
他在《历本议》中论到历法的根本时说: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行变化而通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国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