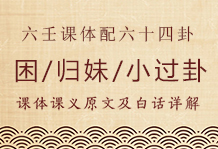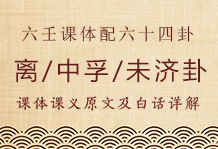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博大精深——治乱兴衰的规律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代表一种“时”,这种“时”是由阴阳两大热力错综交织所形成的具体的形势,象征着社会人际关系的状况和势力的消长,因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主要是表示社会政治秩序由冲突到和谐或由和谐到冲突的动态的过程。它总揽全局,从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制约人们的行为,不是人们所能随意左右的,但是其中蕴含着一种必然之理,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所以这种“时”又叫作“时运”“时义”。人们对“时运”“时义”的认识,目的是为了用,即根据客观形势来决定主体的行为,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动,将导致灾难,所以这种“时”又叫作“时用”。
就一时之大义而言,有时大通,有时否塞,有时正面的势力上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时反面的势力上升,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社会政治秩序的这种动态的过程旱现出一种治乱兴衰相互转化的规律。但是,人们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如果对规律有正确的认识,行为得当,尽管形势不利,也可以化凶为吉,相反,如果估计错误,行为不当,尽管形势有利,则会带来凶的后果。因此,《易传》对规律的研究,其着眼点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强调人们在,总揽全局的治乱兴衰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应该时刻警惕危惧,自觉地承担道义的责任,不可掉以轻心。北末李觀在《易论》中曾经十分感慨地指出:“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

所谓“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不仅是李觀通过个人切身的体会所总结出来的读《易》法,也是历史上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奉行的读《易》法。就《周易》的本文而言,它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为矛盾冲突、混乱失序的现实的困境所激发,焦虑不安,忧心如焚,力求通过客观冷静的研究找到摆脱因境的出路,拨乱反正,化冲突为和谐,变无序为有序。因而《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既有对客观形势的理性的分析,也有对和谐理想的执着的追求,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的结合,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
后世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但是为了寻求拨乱反正的途径,汲取摆脱困境的政治智慧,往往是抱着如同李觀所说的“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去研究《周易》的。《周易》在后世之所以一直享有辞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崇高地位,主要是由于人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比较,一致公认在所有的典籍中,唯有《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最能帮助人们拔乱反正,去建立一个符合人们理想的天地爻泰、政通人和的秩序。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是拨乱反正一词的最早的出处。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提倡,《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人们都推崇《春秋》,从中寻求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司马迁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也十分推崇《春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但是,当司马迁把《春秋》和《周易》这两部经典做了一番认真仔细的比较之后,终于承认它们在拔乱反正方面有着不同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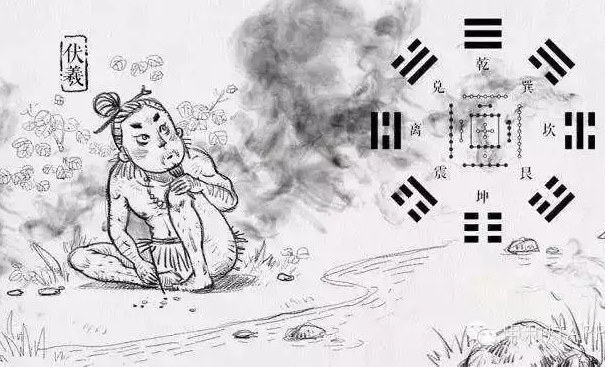
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司马迁指出:“《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这就是说,《春秋》是通过一些具休的历史事例来表明其中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周易》则是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揭示具体的政治操作所遵循的规律。司马迁言下之意,可能是认为,拿《周易》来与《春秋》相比,《周易》的哲学思维水平更高,对于拨乱反正的指导功能更强,给人的政治智慧的启发更大。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做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六艺之文,《乐》偏于仁,《诗》偏于义,《礼》偏于礼,《书》偏于知,《春秋》偏于信。“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班固推崇《周易》的看法与司马迁类似,代表了汉代人的共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中,《周易》所享有的辞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