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以“明于天人之分”而著称的卓越思想家,他对天人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光辉思想
古今学者都认为,“天籁”并非“别有一物”(郭象注);亡不在“人籁”“地籁”之外,就在“人籁”“地籁”之中。由此看来,《大宗师》所说的“畸于人面侔于天”,《田子方》所以说的“遗物离人而立于独”,《天下》所说的“以天为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脫于万物”,都在描述一种“真人”的境界。这种境界,否定了人为,否定了异化了的人、世俗的人,从而进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达到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境界。应该说这是庄子哲学的根本旨趣。庄子哲学虽然旨在为世人提供人生的良方妙道,要人们效法自然,饭依自然,但进人这种境界的人已经不是自然的附属物,而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庄子笔下的“真人”“至人”“神人”“天人”“乘之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道遥游》),“与万物为一”(《齐物论》),“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都极大突出了人的主体精神、生命意义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于是,庄子所谓的“人于寥天一"(《大宗师》)也就不是简单的“天人合一”,而具有高扬主体精神,肯定自由的文化意义。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以“明于天人之分”而称著的卓越思想家,他对天人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光辉思想。首先,针对商周以来的神学天命观,荀子明确指出,天不是有意志的神,而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天行有常,不为光存,不为桀亡,应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军,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安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明于 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荀子强调,自然和人事务有自身的规律,它们两相分立,互不相涉。人类活动符号实际,则自然界的灾异不能给人类造成祸害;反之,人类活动违反实际,自然界也不能给人类带来福花。简言之,社会的治乱,人生的褐福,与自然界(天)无关。这就在肯定自然规律的容观性的同时,把自然与人事区分开来。其次,荀子进一步指出,天与人相分而又相与,人与天的并立,不是向天争夺职能,而是利用自然,造福人类,从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领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熟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熟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熟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物之所以生,執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荀子并没有机械地割断天与人、自然与人事的联系,认为人类具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应该发挥主观能力,向自然素取,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既不同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笼统认识,也不同于庄子的既向自然皈依,又在精神领域追求超越。苟子把儒家的强调人为和道家的重视自然结合起来,其主导思想是要求人仃“应时”“理物”“制天”“利人”,即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制天命”以“应天时”为基础。这就是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深刻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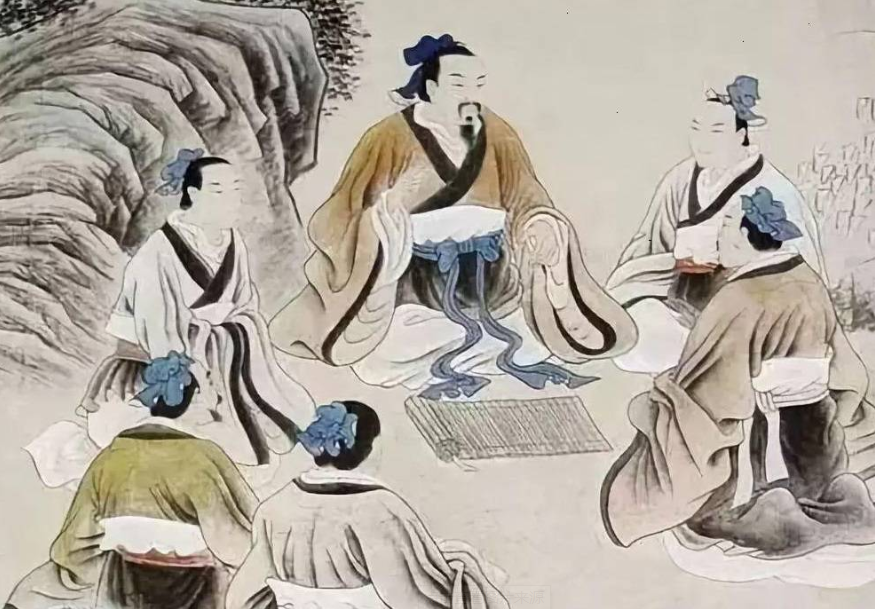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围绕天人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人的讨论,取得多方面的思想成果;或者赋子天以客观自然界的物质意义,把天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在根本上否定了商周以来的神学天命观;或者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给“天”的概念输人了人的意志、人事的义理;或者为了追求个体人的绝对自由,把“天”(自然界)视为人的主观精神驰骋的疆场和遨游的空间,,或者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明确提出“天人之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掌握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光辉思想。在天人关系上,他们分别攀上各自的高峰,取得了不同的思想成果,当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这就给以讨论“天道”和“人道”为骨架的《周易大传》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周易大传》继承其成果,突破其局限,对“天道”和“人道”做出进一步的深刻论述。
这就是我们评论《周易》有关“天道"“人道”思想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