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神至上,王权神授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彖》传在这里表现了自然天道观和神学天命观两相兼顾的思路。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由《彖》传对《革》卦卦辞的解释得到进一步证明: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草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華》之时大关哉。
文中第一句天地连文,毫无疑问,天是自然之天。下文“顺乎天而应乎人”,天人相对,很显然,这里的“天”同上面“天地”连文的“天”不同,是天神之天。“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作者沿袭周初人的观念对“汤武革命”的评价。 “不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孟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戒殿,诞受厥邦厥民《尚书•康诰》。这是周人对周代殷命的权威解释。“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彖》传对周人解释的发展,表现出兼顾上帝与自然、天神与人民的理论思路。

这种兼顾自然与上帝的理论思路,可以说是《周易大传》的共同倾向。《系辞》:
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指著草。下文又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系辞》认为,蓍草的不同排列,变化莫测,神妙非常,定非自然而生,乃上帝有意所为。圣人取菁草,造筮法,成《周易》,指示人事,趋吉避凶,即所谓“以前民用”。这是明显的神学世界观。但开头却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表现出自然规律与人事生活相对应、相统一的思想。《系辞》的这段文字,既是“神道设教”的注释,又是《彖》传自然与天神兼顾的思想倾向的证明。
《彖》传“神道设教”兼顾自然与天神的思想倾向,反映着《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双重内容。在后世,这种倾向分别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进一步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有方式,阐释人事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当以《吕氏 春秋》为代表。这部杂家之言,在天人关系上,承继着《周易》“神道设教”的兼顾倾向,而侧重于“法 天地”。揭明该书宗旨的《序意》说:“上古之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全书以十二纪为纲,编造了一个综括天文地理人事相互关系的世界图式,以时令统率行政活动。
尽管这部书有形式上拼凑、内容上羼杂等缺点,但它提出的“法天地”命题的内容是明确的,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措施效法天地提供了理论基石。
另一方向是沿袭商周时期神学世界观,宣扬王权神授,这当以董仲舒为代表。
这位封建时代的神学理论家,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反复地、多角度地阐述一个主题:天神至上,王权神授。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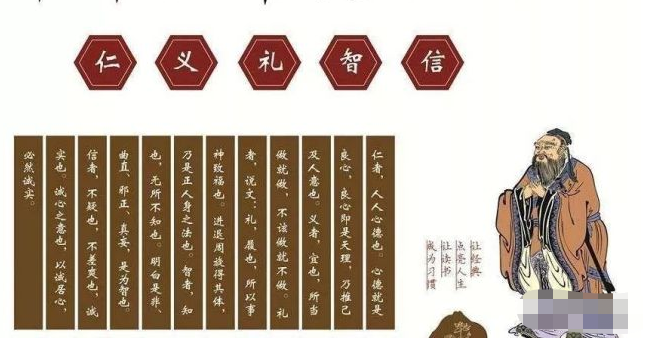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人者天》)天是至上之神,是人间最高主辛;帝王受天的命令来统治天下。他又说:“王者配天,谓共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通有也。”(《四时之副》)“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
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若合符。”(《四时之副》)这就是说,君主施政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合。在《五行逆顺》中他还要求政令与地之金木士水火五行相配合。这样,他就把阴阳五行理论纳人了天命神学的体系之中。童仲舒的政治哲学与《吕氏春秋》的哲学倾向,虽然不同,但兼有法自然之天的思想又是一致的。综合两者,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哲学的两大支点:王权神授和天人感应。而这两点都可以从《家》传的“神道设教”得其近源。《周易》以卜筮之书被封建统治者列为五经之首,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弥纶一切、冠冕群言的地位,主要是“神道设教”从根本上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神道设教”,配合着“王权神授”的思想,借助于天神,宣告封建王权是不可动摇的,所谓“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神道设教”又蕴涵着“天人感应”的观念。
它套用“同类相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治乱兴衰、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荒嘐的,但给人以合乎事理(自然规律)、合乎人情(喜怒哀乐)的假象,因之,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成了历代帝王“仁政”的体现。《周易》给中华文化所提供的首先是这样一个封建政治统治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