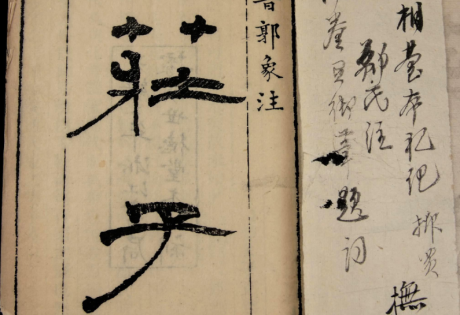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诚,此小人之福也
《易传》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思想倾向毕竟不同于卜筮巫术。在《易经》中,表示休答的词语触目可见,却没有出现一个义字,说明卜筮巫术只关心行为的后果是否与己有利,不考虑行为对群体的影响,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而《易传》则引进了伦理规范和道德义务的思想,从天下之公利和一己之私利的角度明确地区分了君子和小人。《系辞》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诚,此小人之福也。”“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禁民为非日义。”小人“不见利不劝”,是说小人如果不看见利益就不会劝勉行善。但是,小人对利益的追求往往违反了社会共同的行为淮则,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以致走上罪恶的道路,对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因此,必领用义的规范来制约。这种制约只是“禁民为非”,把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引向对社会产生良好影响的正道,而不是根本否定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易传》认为,这种“禁民为非”的做法把小人之私利和社会之公利结合起来,归根到底是“小人之福”,也就是义。君子与小人不同,始终是以社会之公利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即“吉凶与民同患”,这种行为当然是合乎义的。由此看来,《易传》判断行为的标准除了功利的原则以外,又引进了义与不义的原则,即道德义务的原则。

《易传》认为,这种道德义务的原则是必须恪守的,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使之变为自觉的行动。《乾卦•文言》说:“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坤卦•文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但是,恪守道德义务本身就能达到功利的目的,义与利并不像儒家所理解的那样,相互排斥,彼此矛盾。因此,《易传》往往是同时用义与利两个原则来衡量人的行为。比如《解卦•初六象》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鼎卦•九三象》说:“鼎耳革,失其义也。”《渐卦•初六象》说:“小子之厉,义无咎也。”《旅卦•九三象》说:“以旅与下,其义走也。”《既济卦•初九象》说:“曳其轮,义无咎也。”这些说法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义中自有利,不义则不利。前文所引述的朱熹、俞琐对《易传》的解释即据此而来,并非亳无凭依。
这样说来,义就是利,利就是义,儒家只看到前者而没有看到后者,墨家用“贵义”“重利”两个命题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是与《易传》的这个思想相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到哲学的层次做进一步的考察,可以看出,《易传》与墨家也有很大的不同。《墨子•贵义》说:“万事莫贵于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光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架纣幽厉者舍之。”墨家的理论基础是所谓“三表法”,判断行为的标准除了功利的原则以外,还有历史上的圣王之事以及虚幻的天鬼之志,这三个标准并没有在逻辑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易传》则把义与利统一在阴阳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比墨家要高了一个层次。
我们再仔细体会一下《易传》的两个命题,“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其中两次都提到“和”宇。和就是和顺,阴阳两大对立势力协调共济,相因相成,阴顺阳,阳顺阴,构成天人整体的和谐,义与利就统一于此整体的和谐之中。

《易传》是在阐发元亨利贞四德时讨论义与利的关系的。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元亨利贞四德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既表明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自然的和谐,也给人类社会启示了四种伦理规范,即仁、礼、义、智(或信),而要本归于和顺。《乾卦•文言》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元之伟大在于以美利利天下,其所利之物无所不包,这就是所谓“利物足以和义”。因而利就是义,义就是利,不能利物则不足以和义,不能和义则根本谈不上利物,这是一个统贯天人的总的规律,揆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易传》也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来处理的。利是就行为的效果而言的,利必合于义。欲是就行为的动机而言的,欲必合于理。王弼在《周易注•解卦六二》中指出:“义,犹理也’。”义就是理。这个理即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的本质在于和顺。《易传》并不否定人有爱恶之欲,只是强调爱则相取,恶则相攻,相取则阴阳和顺而合于理,相攻则阴阳冲突而悖于理。《系辞》说:“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威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社会的动乱沖突都是由彼此相恶子1发出来的,只有彼此相爱,社会人际关系才能团结合作,协调稳定。《损卦 •象传》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室欲。”这种忿欲是一种彼此相;恶之欲,必领惩止室塞,防微杜渐。至于彼此相爱之欲是合乎性命之理的,应该发扬光大,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因此,易学中的义利,理欲之辦,都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来考察,表现了鲜明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