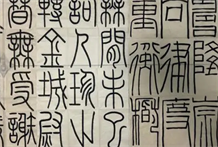大衍之数五十的来历:为什么大衍之数是五十?
大衍之数五十
先看“大衍之数是五十”的一类解释。汉代《易》学大家京房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即是说,“五十”是由天干十,地支十二,星宿二十八相加而成。此说取材全用天文常识,合乎“观象作卦"的思想,干支记历数在殷商就已存在,甘八宿(恒星)位置的确定在西周已经完成,这与《周易》产生的时间并不矛盾。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日干,地支、二十八宿”与八卦及大衍成卦法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使得古人要用这三者的合数来作大街之数呢?这里并没有答案。《周易乾凿度》的解释是:“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凡五十。与京房说法一样。
马融提出:“易有太极,谓北辰。北辰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为五十。” 马融也是想用客观自然本身的内容来解“大衍之数”,所不同的是,他描述了一种罕见的宇宙生成论,四时不生十二月,反生出五行,再由五行生出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本是确定季节时令的标志,他反说十二月生二十四气。这个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但马融的独特处在于,他认识到八卦生成程序与宇宙生成程序的统一性,从而希望在这种统一的程序中找到大衍之数。这显然是高于别人的认识,因为八卦生成说就是《易》学系统中的宇宙生成说!
他的思路显然大有合理性。
郑玄提出了另一种解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以五行气通于万物,故减五。”即大衍数五十是由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减去“五行"数“五"所得。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可以“成变化,行鬼神"的天地数为何偏偏要在减去“五行数”之后才能作大衍数呢?如以五行而论,万物都不离五行,何不直接用这“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的五行数来作大衔数呢?郑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这个解释中,他认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与“大衍之数五十"是有必然联系的。即大衍之数是由天地之数变化而来。这里他已将“天地之数”与“五行之数”连在一起。“五行"之说早在殷商就已存在,箕子在《洪范》“九畴”中把它列作第一项。就时间上看,把五行数作为大衍数形成的一个根据似乎并不矛盾,但五行与《易》最初却是两个系统。《易》占是阴阳之学,伏羲时代就已创立,五行之学虽也源于天文,但大概不会比《易》学早。而且先秦象数《易》学中并没有融人五行学说,易》占中融人五行到汉代才正式展开。因而,象数《易》学与五行在先秦仍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内容,这是“天地之数”(属《易》学系统)与五行数没法联结混同的一个根源。然而郑玄的这个解释在《易》学史上却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荀爽说:“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二用,凡有五十。”这个说法似乎只是在凑数,六爻卦共有六十四个,为什么只用“八”;八卦也可以是三爻卦,为什么偏用“六”;又为什么要"加乾坤二用”?都没根据。
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上》中说: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故著以为数,以象两两之,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孟康曰:“岁有闰七分,分满十九,则为闰也”),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扬再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轨道相错,故有交会。交会即有干陵胜负,故生吉凶也。"),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孟康曰:“天终数九,地终数十。穷,终也。言闰,亦日之穷余,故取二终之数以为义)。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以会数乘之,则周于朔旦冬至,是为会月(孟康曰:“会月,二十七章之月数也,得朔旦冬至日与岁复。”),九会而复元(孟康曰:“谓四千六百-十七岁之月数也,所谓元月。”),黄钟初九之数也。
这个雉法解说可谓奥义汪洋,涉及要素有:元始(道)、春秋、三统、四时、五体、闰法、月法、会数、会月、朔望之会、元(月)、黄钟。班固企图用历法解释筮法,他显然知道“易乃天文”这个道理。但汉历已较为科学,远不是西周的历法,“十九年七闰"实际形成于春秋末期。至于“朔望之会”、“会数”、“会月”、“元月"等更为精确的数字公式,当然也不会是“五岁再闰"历法的内容。至于“黄钟初九之数”这种“历”与“律”的统一,更不会早于十九年七闰的历法而出现。班固显然是在用后来出现的东西去附会解释早先就有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就不能通过。并且提出,“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国法”,意即天数的最后一位是“九”,地数的最后一位是“十”,因为“易穷则变"的道理,所以把天地两类数的穷尽之数合起来的“十九"就成了天文闰法的数。这显然是个附会之说。后面的用天地两类数演绎各种会数,也还是个附会法。试想,天地间的宏观常数有哪些能逃离十个自然数所能演绎的范围呢?班固企图用后来的历法解说先有的筮法,这种做法反不如说是在附会《周易》成卦法的“妙用”。后世众多的《易》学家们也都是循着班固留下的这个附会思路作文章。
至于大衔数五十的来历,班固认为是“以五乘十"所得,那么为什么要“以五乘十"呢?班固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而且在他的“五体”说里(“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五也。成五体”),汉代谶纬附会解经的做法已很明显、其实,“春秋”、“三统”、“五体”与《周易》筮法又何曾沾边。班固的这个“大衍之数五十"的解说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这里并没有把“大衍之数五十"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联系起来,这表明,在他看来,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五十有五”并非大衍之数。
后魏关氏继承郑玄的思路,发挥自家的见解说:“不止法天地,必以五行。大耦则五十,小奇则五,天地之数举大而去小,小奇之五虚而不用。"
他断定著法不只是取法天地,而且涉及五行,表明他并不知道《易》学的根本法则。他把天地之数“五十五”划作两部分:大耦五十,小奇五。认为“大衍之数五十”是“举大去小”,所以天地之数去五不用。这更是纯属想当然。
崔憬说:
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既百著数,则是说大衍之数也。明倚数之法当参天两地。参天者,谓从三始,顺数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两地者,谓从二起,逆数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数也。良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八卦之数,总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不取天数一地数四者,此数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着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著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数,以守其位,故太一亦为一数,而守其位也。
崔憬把《说卦》所说的“参天两地而倚数”与“大衍之数"联系起来,并作为“大衍之数"产生的根据,这确实有独到之处。他对“参天两地"的解释也很独特,其实质是取法“九宫八卦数”中的对应规律,即“阳进阴退”,九宫数即所谓“洛书数”,卦位是取法《说卦》中的文王卦图,即所谓“后天八卦图”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与九宫数不同的是,崔憬加人了“十”,去掉了“一、四”,认为八卦中的“二少”(即阳艮阴兑)起数应该从“三"和“二”开始,“艮三”“兑二”,因为“参天两地而倚数”。之所以去掉“一、四”是因为阳卦起数从“三"开始,顺数,到五、七、九,已配完四个阳卦,所以不用“一”;而阴卦起数从“二"开始,逆数,到十、八、六,已配完四个阴卦,所以不用“四”。这显然没有依据,是崔氏的创造。这样,他得出了“八卦之数,总有五十"这种“大衍之数"形成方式。他的大衍之数五十在本质上仍是来源于天地之数,是天地十数除去“一、四”所成。他又认为,用策四十九是取法“长阳七七”是天圆之说;卦数六十四是取法“长阴八八”,是地方之说。此中附会确很精妙,然而数图方圆任由人心,宋人后来就发挥得很透彻。崔的这个解释的价值在于,它用了企图依据经典本身寻找问题答案的思路。由于崔憬的做法中有明显的勉强内容,所以李鼎祚在案语中就说:“即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 然而李氏随即转入了郑玄的思路,认为大衍之数是天地之数减去五行数所得,并说:“其用'四十九’者,更减一以并五,备设六爻之位,著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同属牵强之列。
《易数大略》说:
大衍者,八卦之衍数也。八卦经画二十四,重之则四十八。又每卦各八变,其爻齐四十八。是四十八者,八卦之正数,衍其正数,是谓大衍。衍,羡也。以四十八而羡其二,则为五十之成数。
该书把“衍”解作“羡”,认为“五十"是“四十八”“羡二”所得,这显然奇特。它又提出“四十八"是“八卦正数"的说法,并说“每卦各八变”,这更是荒谬了。每卦变法岂止八样。这个解释也是企图从八卦自身寻找大衍之数的依据,从逻辑上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八卦是由大衍之数五十筮得的,善数与卦爻数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这个联系究竟怎样,这就不是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所能解决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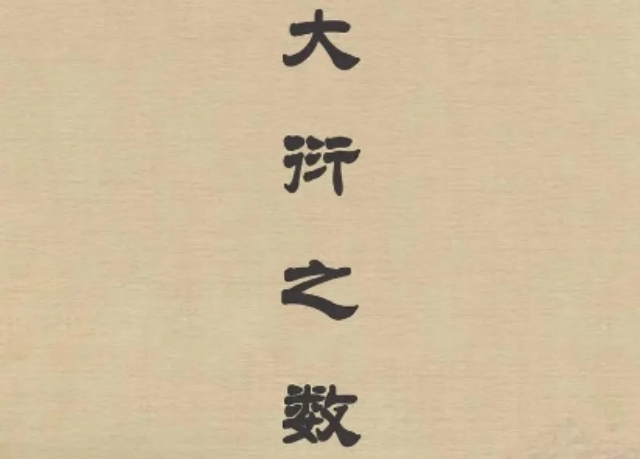
赵汝樣又述宋人的解释说:
程氏曰:数始于一而备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则为五十。
龟山杨氏曰:天地之数备于五。其十也,以五成之。
吕氏曰:参天两地以为五,小衍之为十,两其五也,大衍之为五十,十其五也。
以上三说属一系。程氏所谓“数始于一而备于五"是指五行数(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由于五行数中从“一”到“五"称作“生数”,从“六”到“十"称为“成数”,所以程氏说,数从“-"开始,到“五"就完备了。由它们可以演变出各种数来。但他接着造出“小衍”、“大衍”两个概念。由吕氏所作的解释可知,“小衍”是“两个五”,“大衍”是“十个五”,那么处在“小衍”与“大衍"之间的“三个五、四个五…九个五”,怎么称呼呢?程氏就没再发明了。龟山先生阐扬师说,认为“天地之数备于五”。数到五就已完备,这原是古人的“生数"说,但龟山先生认为“天地之数”到五就已完备,与《系辞》明确记录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思想就不能相通了。“五行生数”并不是“天地之数”,“天地之数”共有十位,不能“备于五”。吕氏比杨氏要聪明些,为了统-“五行生数”与“天地之数”,他提出“参天两地以为五”,即从一到五的五个数中,天数有三个(天一、天三、天五),地数有两个(地二、地四)。这样就贯通了“五行数”与“天地数”,但同时也就会聚了二数各自与大衔数之间的矛盾,而且引发了新的疑问:“大衍之数五十”与“五行生数"结合,立论依据在哪里?结合方式的确定(五乘十)的依据又在哪里?“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有联系的依据是什么?联系方式(五十五减五)的确立依据又是什么?吕氏贯通了“五行生数”与“天地之数”的前五位,剩下的后五位又怎么办?如果说后五位同样可以贯通,用“成数"(六、七、八、九、十)来解决,那么无疑等于说“天地之数"可以用“五行数"来取代,《系辞》为什么要说“天一,地二,天三,……天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可见,以上三人之说实质上是汉代郑玄对大数解释方法的变种,是换着法子建立起“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五行数"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已。这当然是《易》学行至宋代早已与五行学说相融合,致使宋人已不知《易》数与五行数各有源流的结果,无视二者之间的本源性差别,牵强解释,当然只会带来问题的更加混乱。而就是这种混沌解释,赵汝竟作评语说:“右大衍五十,吾圣人发之程子明之,遂可辨万世之惑,迪万世之明。”不知是生性爱说胡话,还是存心欺世!
又有司马氏曰:“易有太极,一之谓也。分为阴阳,阴阳必有中和。故一衍之则三,而小成,十而大备。小衍之则六,大衍之则五十。”在这个解释中,提出了一个“阴阳必有中和”的说法,并设定这个“中和”也是数一,所以由太极的“一"衍出了“阴、阳、中和”的“三”,这叫“小成”。它又提出“小衍”是六,“大衍"是五十,这显然是与程氏不同的又一种“衍"法。
元代雷思齐又提出一种解释说:
有是而观,则易之有太极,而太极者特浑论之寄称尔。浑论而上,既有谓易,谓初,谓始,谓素,凡四其称,而至于浑沦而五,故以浑沦为太极,是之为五太也。是则太极也者,既先含其五于中矣。故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乃五十者,既虚其太极已上之五,而取用于五十之妙也。
雷氏是用《易纬·周易乾凿度》的思想在注大衍数,周易乾凿度》曾说:“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但这是汉人创造的宇宙生成论中的新说法,是糅合《易》与老庄而得,这在前文已有论说(《筮数阴阳爻化》章第二节),雷氏拿它来解释大衍数,显然是忽视了《易纬》的可靠性程度。雷氏是说,易》的太极就是“浑沦"的别称,从太易到太初、太始、太素、浑沦,共五个形式,是“五太”,太极中先已包含了这五种形式,所以大衔数是用“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去掉太极以上的五而得。以上各种解释无论有据与否,都还有一定的理路。在认为大价数是五十的解说中,还有一些近乎荒谬的解释,这里选择-二以观大概。赵汝樣《筮宗》里有二说:
张氏曰:天数二十五,合之则五十。
希夷陈氏曰:物数有进退。人寿百数,前五十为进,后五十为退。大衍者,半百之进数也。
清人冯道立在《周易三极图贯》中也有一说:
考《洪范》数,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五皇极,六三德,七稀疑有七,八庶征有五,九福极十有一,合之成五十。其一不用者,皇极也。皇极即太极。太极惟一,皇极亦惟一。大衍太极之一不用,九畴皇极之一亦不用!一即是-。《洛书》与《河图》,先圣后圣,其换一也。”(并附有图)
认为大衍数五十来自《洪范》“九畴"所说的各类事项的条目数的总和。其实这-说法早在《易学启蒙·本图书》中已有,而且娓娓有据。虽然新奇,未免荒诞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