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无民,何有君:国无民不立,重视人民,是为了立国;保民,是为了统治
早存两周初年,刚刚推翻般商政权取得统治地位的周王朝的统治者,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重视民心比敬畏天命更具现实意义,提出了“哀(爱)于四方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召话》),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民本思想的传统。春秋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几乎成了统治阶级的普遍认识。“民和而神降之福”,“国将兴,听于民”,“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的议论,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爱人"泛爱众”等主张,用心理上、情感上的人道原则来调整、维护处于崩溃局面的宗法 等级秋序。其政治上的意义是反对过分的、残暴的压迫和剩削。经孔子提信,民本思想广为流行,并为封建统治者肯定、按受。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本思想为需家所独有。略先于孔子的道家老子就说:“费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 •六十六章》)他所谓的“费”“高”,指统治者(王侯);他所谓的“贱”“下”,指被统治者(人民)。接下来,他又说:“是以圣人秋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同上)略后于孔子的墨家创始人墨翟主“兼爱”,倡“非攻”,建立了白己独特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从“贱人”(被统治者)出发,但其宗旨是天下之民上同于天子。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政治实践的产物,是不同学派观察君民关系、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成果。多数封建统治者肯定民本思想,许多思想家宣扬民本思想,并不是给被统治的人民以政治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国无民不立,重视人民,是为了立国;保民,是为了统治。战国时期的赵威后就说过:“苟无民,何有君。”(《战国策• 赵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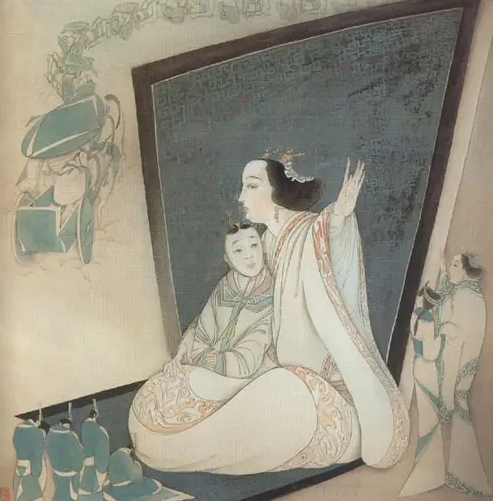
还是老子说得最透彻:“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提倡民本思想,是封建君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我们对《周易大传》的“化民”“保民〞定民”,亦应作如是观。
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在战国时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来,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着由缓慢进而急剧的变化。领主经济逐渐为地主经济所代替;与之相应,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其中,重要的是,原来农奴身份的下层“贱人”在经济关系的变动中获得解放,统称之日“民”。这时的“民”大大不同于春秋以前的农奴阶级,已是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自由民。他们由经济束缚的解脱,进而要求政治上有所作为,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墨子的“尚贤”和孟子的“民为贵”。关于墨子“尚贤”,上文已有简略评述,简要说来,它反映着被统治的人民参与政权的要求。这就为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然,墨子的政治思想是矛盾的,他既为下层“贱人”呼呼,又为统治者谋划。这个复杂问题,非本书讨论的内容,兹存而不议。关于孟子的“民为贵”,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光辉命题。他向当时残害人民、盘剥人民的统治者慷慨而郑重地宣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联系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高姿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等言论,我们不能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仅仅是民的问题比君的问题重要;还应该看到,这是在理论上(也只能在理论上)把传统的君贵民轻的观念颠倒过来,从而把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的境地,以致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的众多民本理论难以逾越的制高点,直至今天,还放出耀人的光辉。《周易大传》基本形成于战国晚期,它融汇了需道阴阳各家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似乎它的作者们在政治上比较迟钝,没有感受到民本思想的新发展,可以说依然固守着西周以来民本思想的老框框。这在浪涛激荡的战国时期的民本恩潮中,未免显得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