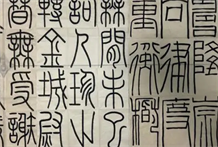《归藏》筮数中的“一"是阳爻符号:筮数展示出的是一种无规律性,它反映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
《归藏》筮数中的“一"是阳爻符号:筮数展示出的是一种无规律性,它反映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
在上述八个涉及四种不同筮数符号的卦中,除了上述两个《归藏》卦外,还余下六卦,晚商3号是六六七六一八,周代1号是六八一一五一,2号是五一一六八一,11号是七六六七一八,13号是六六七七一八,29号是一七六七八六,这里除了筮数五、六、七、八外,多出来一个"一”,这些卦又属于什么筮法呢?无论是《周易》,还是《归藏》,都不可能出现筮数“一”(事实上,《连山》筮法也不会产生筮数“一”,《连山》筮数是“七、八”,下节有叙)。
也许有人要提出,既然四川凉山彝族曾有过“雷夫孜"占卜法,就不能说没有产生这种筮数为“一"的筮法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存在的前提是“雷夫孜”占卜法,对于夏商周已建立起强大政权,有专门机构掌管天文,司掌筮法,传授筮法的时代来说,天地之道决定万物的思想早已成了社会中的支配观念,“易与天地准”作为筮占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早就存在,决不会在中央政权中还运用某种极其原始的,带有随意性和无规律性的筮法,何况卦表中的所有筮数都在“五、六、七、八、一”这五个数字符号的统一中,而且每卦涉及的筮数符号最多不超过四个,这里所呈现的规律性是不能运用任何偶然和随意来解释的。这个“一"只能是属于三《易》筮法的内容。
而在上表的36卦中就有21卦内有符号“一"。从表中看,“一"早在晚商就出现于卦中了(见商代2、3号卦)。再据张老对周代32卦的筮数统计,列表是:
筮数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次数36 0 0 0 11 64 33 24
这个次数表说明了周初“一”这个符号使用的频繁。而在后来陆续出土的数字卦材料中,这个"一”出现的频率依然非常高,出现的次数更是明显增加。从晚商、西周的卜骨、青铜器上的数字卦到东周的包山楚简、王家台秦简、阜阳汉简中的《易》卦,直至今日所见的《周易》卦画卦图,都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根据《周易》筮数是六、七、八、九来看,诸卦中又没有“九”,这个“一”是否就是“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些只含有“六、七、八、一"的卦(或者只含有其中的几个数乃至一个数字符号的卦)就有可能是《周易》筮卦。然而在上表中周代的1号(一五一一八六)、2号(一八六一亠五)、23号(一五八)、32号(一一五)
四卦中都是“五”与“一”同在,“五”和“九”同时出现在《周易》筮卦之中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情况说明这四卦不可能是《周易》筮卦,这里的"一"不是"九”(据此也可以推知,这一时期的“一"大概不会是筮数“九”)。至于那些不含有“五”但含有"六、七、八、一”的筮卦是否一定是《周易》筮卦,还得结合《周易》产生的时间和这些数字卦的占辞所展示的解占方法来考察判定,而不能简单草率地下结论。事实上,据张老考证,“古筮的考古资料,从殷墟三期(约廪辛康丁时)到西周早期(约穆王时止)皆数止于八,没有出现过九字”Φ,“殷及周初的筮数中不见‘九’字","九"字出现于“西周中期以后”的考古材料上。据此而论,殷商及周初没有出现“九"字即意味着没有出现《周易》筮法的卦。所以,这一时期带有符号“一"的卦仍不是《周易》卦。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商代及周初存在一种可以产生“五、六、七、八、九"五个筮数的筮法呢?据史书记载,股商的筮占体系是《归藏》,周代的筮占体系是《周易》。已经清楚的是,两者的筮数都是四个,就此而论,殷商及周初不大可能还存在一种能产生这样五个筮数的筮法。从出土数字卦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一卦有六爻,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筮法,那么五个相连筮数在一卦之中同时出现的机会应该是不小的,但是,就目前出土的文献看,还没见到一例这样的筮卦,所见筮卦的筮数符号的种类都没有越出四个。因此可以确定不存在这种五个筮数的筮法。不过,存在一种多个筮数的筮卦,但筮数又并不是“五、六、七、八、九",而是“一、二、三、四、五、六”等。这种筮数展示出的是一种无规律性,它反映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与上述明显呈现为规律性的筮数无法相提并论。
对此,本章第四节有详细论述。所以可以确定在上述的数字卦里,符号“一"不是“九”。
“一"从商代出现一直存在于数字卦中,历经殷商、西周、东周、秦、汉至今。这一存在时空上的延续性与它的使用频率增大、出现次数增多的事实表明,"一"在筮占历史中具有继承性,它在内涵上一定存在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内容可以为商、周不同的筮占体系所共同使用。而《周易》体系中的“一”是明确的阳爻符号,据此而论,晚商数字卦中的这个特殊符号“一”应该就是阳爻符号。然而,阳爻展示的只是阳性(筮卦中的奇数)这一性质,没法直接告诉我们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数,而商代《归藏》的筮法与《周易》的筮法又显然不同。“一”在《周易》体系中代表“七”与“九”,它在商代数字卦中又代表什么数呢?这一问题也应是揭示商代筮占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归藏》筮数是“五、六,七、八”,其中表示阳性的筮数有“五”和“七”,如果“一”真是阳爻符号,那么它应该能表示“五”和“七”,而且这种用法在筮占史料上应有体现。出土材料证明,这个推论结论是一种历史真实。“一"在《归藏》中的具体含义可以从出土数字卦中找到答案。
在《包山楚简》的“卜筮祭祷记录”中记载着许多次祭祷和筮占。其中记录有完整卦象.筮占事由及占辞的共有六次,每次都同时筮有两卦。内中陈乙为左尹邵舵进行的筮占共有两次,其中的一次是这样:
(一六五八六六、一六六一一六)。占之,恒贞吉,少又(有)忧于官室。
占辞的意思是:按此卦而论,坚持正道则吉,但于宫殿房屋而言小有忧患。依据占辞来看,是两卦分开而论,前卦(相当于《周易》的《晋》卦)是日光照耀大地,吉利之象,后卦(相当于《周易》的《蛊》卦)有宫殿房屋慢慢朽蔽坍塌之象,故有忧患。”占辞中并没有展示出两卦之间存在主卦和变卦的关系,因而不会是《周易》筮卦。每筮两卦,分开解占,这是古史中提到的《归藏》“贞悔”法则之一。所以这里运用的解卦方法是属于《归藏》占法。据此而论,这一卦应是《归藏》筮卦。再结合数字卦象中的前一卦来分析,这一卦的筮数是“五、六、八、一"四种符号,那么作为《归藏》占法,这里的符号“一"能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筮数“七”。"一"是阳爻符号,在《归藏易》中代表筮数“七”。
“一”作为阳爻符号反应的只是阳性,在数中能表示奇数。那么,《归藏》筮数里还有一个奇数“五","一"是否还代表着筮数“五”呢?从晚商的数字卦来看,它确实代表着筮数“五”。在前表中,晚商的3号卦是八一六七六六,此中涉及的四种数字符号是“一、六、七、八”。这里“一"不会是《周易》筮数“九”,因为筮数“九”字在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于数字卦中,而此卦是晚商时代的卦,是出土于安阳殷墟(商的国都)。因而,这一卦不会是《周易》筮卦,它只可能是《归藏》筮卦。那么,“一”代表的就是筮数“五”。这样,“一”在《归藏易》中既可以表示"五”又可以表示"七”,它是阳爻符号,而不是数字。

至于《归藏》筮数“五、七”为什么写作符号“一”,为什么一卦之中“五、七”要分开与“一“使用,这又涉及到筮数阴阳爻化的问题,后文列专节阐述。
依据“一”既可表示“七”又可表示“五”这一事实来看,在上述卦表中的那些既含有“六”和“八”,同时又含有“一”的数字卦都是《归藏》筮卦。因为《周易》筮数“九”字在西周中期以前还没出现,“古筮的考古资料,从殷墟三期(约廪辛康丁时)到西周早期(约穆王时止),皆数止于八,没有出现过九字"。这表明此时不会有《周易》筮卦。因此,如果前表中关于36卦刻写时间的确定没有错误,那么可以确定它们全部都是《归藏》筮卦。
以上考古材料表明,商及周初的筮数主要是五、六、七、八、一,这说明这一时期《归藏》筮法占统治地位。张老在《易辨-近儿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一文中又进而总结出:“近几年来,又见到许多古筮的考古资料,总共有百十来个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这个材料也证明着《归藏》占法在当时的统治地位。对于“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的现象,只要明了三代筮法,是无须存疑和作别种解释的。因为三《易》筮数中本不含“二、三、四"这三个字。“九”字直到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于考古材料上,此论尚有问题。张老说:
一九八〇年春,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了一些周代甲骨,内有一片卜骨(80F,QEH:108)是西周中期以后的,正面横刻着一个卦贾(一六一六六八),背面在骨脊两旁各刻一行两个卦,左边是备(一八六八五五)鑫(六八一一-一),右边是發(六九八一八六)鲁(九一一一六五)。
认为出现了两个“九”字,并且“是由八改成的”(即X),“这是九最初出现的情况,使用率不高,和后来《易经》所见的九字不大相同,可能不是一回事。””
根据三《易》筮数看,这五卦的最后两卦中,前卦的“九”用《周易》筮数解释没问题,但后卦就有问题了:“五,九"并存于一卦之中,这不可能,而且同一片卜骨上同时使用《周易》筮法和《归藏》筮法,似乎也很勉强。其实,殷商早有“九”字,殷墟出土的“九”字写作“ぶ”,西周大可不必新创“H”这种写法。张老也说,这两个“九”字“和后来《易经》所见的九字不大相同,可能不是一回事。”这两个“”与早先的“)["有明显的不同,西周中期出现这种形体近似于“)[”的筮数,是否表示此时的“)[”有了一种新的含义?
如果说上面的“九”字还有问题,那么1978年春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中期邸阳君番勅墓出土的竹简上出现的“九”字则是明朗而无误的了。然而,这已是战国中期,而《国语》《左传》上的筮例确证着《周易》早在春秋初年已经存在于一些诸侯国中了。考古材料只是历史的遗迹而已。
张老曾在《易辨》一文中还提到一个问题:“从不见‘九'字,到出现‘九’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理论上很难解决,只有用历史解释,我推测是个民族化问题。”